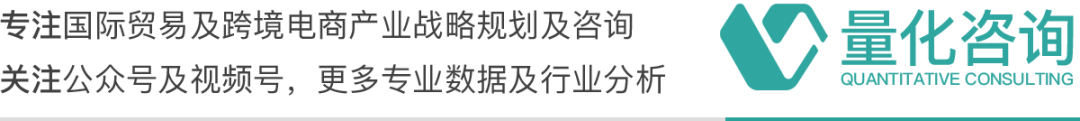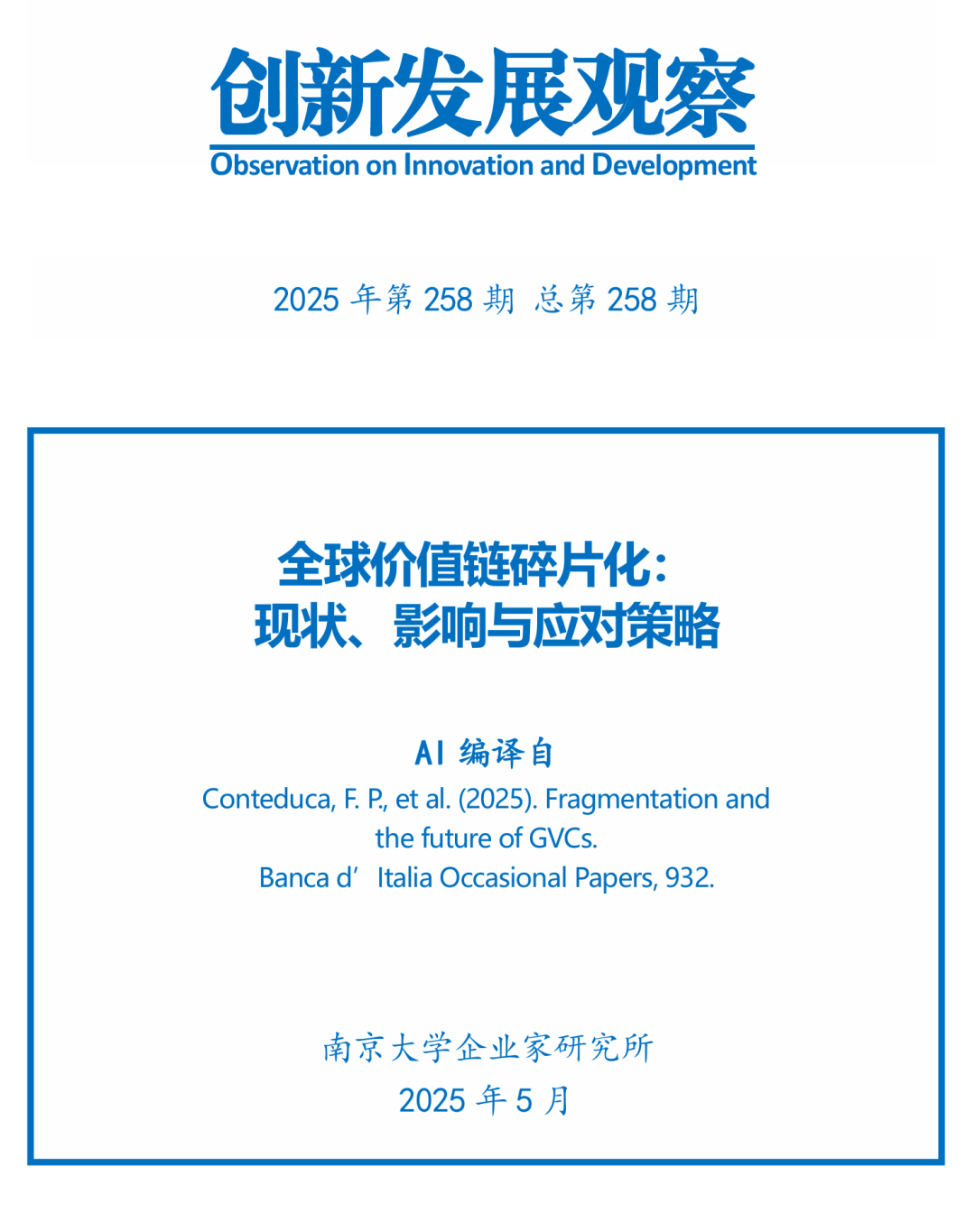
全球价值链碎片化:现状、影响与应对策略
摘要
本文聚焦于《Fragmentation and the future of GVCs》两篇文章,深入剖析 2025 年美国贸易战及全球价值链碎片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2025 年,美国大幅提高关税,对众多贸易伙伴实施“互惠” 关税,导致全球贸易遭受重创。美国自身福利显著下降,“现状” 情景下福利降约 2% ,“全面+ 报复” 情景下几近翻倍;全球福利在该情景下损失达 2%,中国福利损失约 1.5%。同时,全球贸易流量收缩 5.5%-8.5%,美国从中国进口暴跌约90%,中国对美间接出口相对更具韧性。贸易碎片化受地缘政治和政策驱动,研究通过定制模型和投入产出表分析其影响。在不同情景下,各集团福利变化差异明显,东集团在基线情景下福利损失达 1.3%,刚性情景下全球福利和实际GDP 下降严重,东集团损失近 10% 。全球贸易总量收缩约 10%,贸易流向发生改变,集团内部贸易增加。全球价值链呈现区域化、复杂化与隐形化特征,中立国家在价值链中的作用增强。综合来看,贸易战和贸易碎片化对全球经济福利造成双重打击,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冲击国际贸易秩序。未来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各国需在安全与发展间寻求平衡,加强国际合作,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以应对挑战。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全球价值链(GVCs)曾将世界各国紧密相连,推动着国际贸易和经济的飞速发展。然而近年来,地缘政治冲突、贸易政策调整以及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使全球价值链正经历着深刻变革,碎片化趋势愈发明显。这一趋势不仅对各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全球经济未来走向的广泛关注。《Fragmentation and the future of GVCs》一文深入剖析了这一复杂现象,为我们理解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提供了关键视角。
二、全球价值链碎片化的背景与驱动因素
2.1 地缘政治冲突引发贸易政策转向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是全球价值链碎片化的重要催化剂。俄乌冲突、中美贸易摩擦等一系列地缘政治事件,使各国深刻意识到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纷纷调整贸易政策以保障自身关键产业的稳定发展。美国出台的《芯片法案》旨在增强本国芯片产业的竞争力,减少对国外芯片的依赖,确保在半导体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欧盟的《关键原材料法案》聚焦于关键原材料的供应安全,力求降低外部供应风险。中国则通过财政支持政策,大力推动电池生产和电动汽车制造等战略产业的发展,提升产业自主性。这些政策的实施,促使各国在关键领域加强了国内生产,减少了对地缘政治对手的进口依赖,进而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碎片化进程。
与此同时,经济相互依存关系被用作地缘政治的工具,贸易和投资限制成为常见手段。俄乌冲突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多轮严厉制裁,涉及能源、金融、科技等多个领域。这些制裁措施不仅限制了俄罗斯的对外贸易,还打乱了全球产业链的正常运转。俄罗斯作为重要的能源供应国,其贸易受限导致全球能源市场波动,许多依赖俄罗斯能源的国家和企业面临生产困境,全球价值链的稳定性受到严重挑战。
2.2 全球贸易格局的悄然变化
尽管目前尚未出现彻底的去全球化现象,全球价值链的复杂性在近年来也未显著下降,但贸易格局已出现明显的结构性变化。不同行业受到的冲击程度存在差异,部分行业受到的影响较为严重。半导体行业,美国对中国实施的技术出口限制,使中国半导体企业在关键技术和设备进口方面遭遇瓶颈,阻碍了产业的正常发展,也打破了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原有平衡。
在贸易格局变化的过程中,非结盟国家的地位逐渐凸显,它们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连接器” 角色。越南、新加坡等国家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开放的贸易政策,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加强与不同集团国家的贸易往来,促进了贸易在不同集团之间的流通,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球价值链碎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3.1 模型选择与创新扩展
为深入研究全球价值链碎片化的影响,本文采用了 Baqaee 和Farhi(2024)的多国家、多部门模型,并对其进行了创新性拓展。该模型构建了一个非线性的经济框架,涵盖多个国家和多个部门,商品可在各国之间自由贸易,并受到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冲击影响。在原模型基础上,研究团队进行了两方面的重要扩展:一方面,展示了如何获取实际投入产出网络的变化,以便深入研究全球价值链在贸易碎片化冲击下的调整机制;另一方面,将国家间投入产出(ICIO)表进行扩展,纳入微观层面产品的异质性武器化潜力,使模型能够更精准地反映现实贸易中的复杂情况。
在模型设定中,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具有 CES 偏好的代表性消费者,经济体系包含多个部门,各部门具有不同的武器化潜力。生产者运用 CES 生产函数进行生产,综合利用原始生产要素和其他中间投入品。通过构建异质代理投入产出(HAIO)矩阵,详细描述了经济体系中各主体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为后续的深入分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3.2 投入产出表的拆分与细化
传统的投入产出表通常在宏观层面呈现经济数据,难以准确评估针对性贸易限制的影响。为解决这一问题,研究团队提出了一种将投入产出表进行拆分细化的方法。根据产品的武器化潜力,将每个部门划分为具有高武器化潜力和低武器化潜力的两个子部门。对于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分别构建相应的拆分系数矩阵,以确定各部分产品在贸易中的流向和份额。
在实际操作中,利用双边贸易流量数据和 Broad Economic Categories 分类,结合简化假设,计算出中间产品的拆分系数矩阵\(\Gamma^{X}\)和最终产品的拆分系数矩阵\(\Gamma^{C}\)。通过这些矩阵与原始投入产出表的运算,分离出高武器化潜力产品和低武器化潜力产品的贸易流量,进而得到更为详细的投入产出表结构。这一方法使得研究能够更精确地分析贸易限制对不同类型产品和部门的具体影响,显著提高了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四、贸易碎片化的经济影响
4.1 福利变化:不同集团的差异化影响
贸易碎片化对不同集团的福利产生了显著的差异化影响。在基线情景下,全球福利下降约 0.5%。其中,东集团(以中国及其盟友为主)由于在全球价值链中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较高,且受到贸易限制的产品范围较广,福利损失达到 1.3%;西集团(以美国及其盟友为主)凭借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和相对多元化的经济结构,福利损失相对较小,为 0.5%;中立集团则因能够利用贸易集团之间的壁垒,以及自身经济收缩较小,福利有所增加。
在刚性情景下,全球福利和实际 GDP 下降更为严重。全球福利下降4.6%,东集团受到的冲击最大,福利和实际GDP 损失接近 10%。这是因为东集团的许多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关键环节,贸易限制导致其市场份额流失、生产成本上升,经济活动受到严重抑制。西集团虽然受影响相对较小,但福利和实际 GDP 也下降了超过 4%。值得注意的是,中立集团在刚性情景下仍能保持适度的福利增长,特别是在具有较大贸易多元化可能性的情况下。沙特阿拉伯作为石油出口国,在刚性情景下受益于能源商品相对价格的上涨,实现了较大的福利提升。
4.2 贸易流量变化:收缩与重新分配
贸易碎片化导致全球贸易总量收缩,约减少 10%。东集团的贸易流量损失最为显著,约三分之一的贸易流消失。这主要是由于东集团与西集团之间的贸易受到严格限制,许多原本的贸易往来被迫中断。相比之下,西集团的贸易下降幅度相对较小,但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中立国家的贸易流量则出现了增长,成为贸易重新分配的重要受益者。
贸易重新分配现象在不同集团之间表现明显。受限制产品在集团间的贸易几乎停止,转而流向盟友和中立国家。西集团内部贸易增长 7.5%,东集团内部贸易增长更为显著,达到33.6%。这表明贸易碎片化促使各国更加注重集团内部的贸易合作,以降低外部贸易风险。中立国家对东西集团的出口分别增加约 10%,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逐渐提升。非受限贸易流量的变化相对较为温和,主要反映了贸易替代模式和供应链调整的影响。在一些行业,企业通过调整供应链布局,寻找替代供应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贸易限制对生产的影响。
五、全球价值链的结构调整
5.1 全球价值链整合:总体稳定与局部变化
尽管贸易碎片化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冲击,但全球价值链的总体整合程度并未出现大幅下降。通过对一系列常用于衡量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价值增值贸易的标准指标进行分析发现,贸易碎片化冲击后,全球价值链相关贸易(即贸易流跨越至少两个边境的贸易)占比仅略有下降,与过去的变化趋势相符,且与近期趋势保持一致。垂直专业化指数、价值增值出口和国内价值增值出口等指标也基本保持稳定。
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贸易碎片化冲击主要影响特定产品在对立集团国家之间的贸易,而不是全面破坏全球价值链的整体结构。尽管受限产品的全球价值链和非全球价值链贸易均受到限制,但非受限产品的多边境贸易仅受到间接影响。非受限产品可能作为受限产品的投入品,在受限产品受到贸易壁垒限制时,其贸易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波及,但这种影响相对较小,使得全球价值链的整体整合度得以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
5.2 中立国家的角色转变:GVC 贸易的崛起
中立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发生了显著转变,其全球价值链贸易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在贸易限制的影响下,东集团和西集团的部分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下降,而中立国家则迎来了发展机遇。以越南、菲律宾、墨西哥和新加坡为例,这些国家在纺织品、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电气设备等领域的全球价值链出口大幅增长,尤其是在受限产品贸易方面。
中立国家不仅加大了国内生产以满足全球价值链的需求,还积极开展转口贸易,将其他国家的产品出口到受贸易限制影响的市场。贸易限制使得中立国家作为连接不同集团的 “连接器” 角色更加突出,其出口产品的进口含量上升,进一步强化了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中立国家在电子产品领域的转口贸易增长迅速,通过将从其他国家进口的电子产品再出口到受限市场,不仅促进了自身贸易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全球价值链的运转。
5.3 供应链区域化:近岸与友岸外包趋势
贸易碎片化推动了供应链的区域化发展,近岸和友岸外包趋势日益明显。在欧盟和美国,来自东集团的产品市场份额减少后,部分被国内生产和来自其他国家(如欧盟内部国家、加拿大和墨西哥等)的产品替代。在欧盟,约四分之一东集团失去的市场份额被国内生产取代,三分之一以上被其他欧盟国家产品替代;在美国,超过一半东集团失去的市场份额由国内生产填补。
从供应链的重新布局来看,欧盟约一半来自东集团的供应链(以全球价值链相关进口衡量)被欧盟内部供应链所替代,中立国家也吸引了相当一部分重新配置的供应链。美国约三分之一来自东集团的供应链转移到了加拿大和墨西哥,中立国家和欧盟也从中获得了一定份额。这种供应链区域化的趋势有助于企业降低运输成本、提高供应链的响应速度,同时也增强了区域内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
5.4 供应链复杂化与隐形化:间接依赖的增强
贸易碎片化使得部分供应链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监测,间接依赖程度上升。中立国家对受限产品的转出口大幅增加,受限产品从东集团间接通过中立国家流向欧盟和美国的数量在冲击后增加了 15% 以上,中国从中立国家进口来自西集团的受限投入品增长约25%。
以计算机和电子产品为例,这些产品在中立国家的转口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受限产品往往被嵌入其他非受限产品中进行贸易,传统的贸易监测手段难以准确追踪其流向,增加了全球价值链监测的难度。这也表明,标准的贸易限制措施难以完全切断国家间的经济依赖,产品可以通过复杂的价值链结构找到替代路径,维持间接的贸易往来。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总结
本文通过构建定制化的投入产出表和多国家、多部门模型,深入研究了全球价值链碎片化的影响,得出以下重要结论:贸易碎片化虽然对参与集团的福利产生了显著影响,但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并未出现急剧瓦解,全球价值链的整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稳定。不同集团受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东集团在福利和贸易方面受到的冲击较大,而中立集团则在贸易碎片化过程中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机遇。供应链区域化趋势明显,各国更加注重区域内的经济合作和供应链重构;同时,间接贸易依赖的增强使得全球价值链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监测。
6.2 政策建议与未来展望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各国在制定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全球价值链碎片化的影响。对于受到贸易限制冲击较大的国家,应积极推动产业升级和多元化发展,降低对特定市场和产品的依赖程度。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通过拓展新兴市场和发展国内市场,减少贸易风险。对于中立国家,应进一步发挥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连接作用,加强与不同集团国家的贸易合作,优化贸易政策和营商环境,吸引更多的贸易和投资。
从全球层面来看,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贸易争端,避免贸易保护主义的进一步升级。推动全球贸易规则的改革和完善,使其更加适应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新趋势,促进全球贸易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全球价值链碎片化对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的差异化影响,以及如何制定更加精准有效的政策来应对这一挑战,为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在全球经济格局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各国需要在保障国家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积极适应全球价值链碎片化的趋势,通过合作与创新实现共同发展。
本文引用格式与著作权如下
Conteduca, F. P., Mancini, M., Romanini, G., Giglioli, S., Borin, A., Attinasi, M. G., Boeckelmann, L., & Meunier, B. (2025). Fragmentation and the future of GVCs. Banca d’Italia Occasional Papers, 932.